苏珊·桑塔格:"中国病毒"的刻意污名,体现着怎样的西方逻辑?
苏珊·桑塔格:“中国病毒”的刻意污名,体现着怎样的西方逻辑?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公开将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这种刻意的污名化称谓,究竟体现着包括特朗普在内的一些美国政客怎样的目的与思维逻辑?在此之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曾表露出对类似“武汉病毒”等名字的不满。世卫组织将本次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称为COVID-19时,他就提到,这不仅是为全球提供了一个标准,还能通过使用这个名字,去避免使用另一些污名化的称谓。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在其著述《疾病的隐喻》中的相关论述值得我们深思。
【文/苏珊·桑塔格】
对瘟疫的通常描述有这样一个特点,即瘟疫一律来自他处。当梅毒在十五世纪最后十年以流行病的形式开始肆虐整个欧洲时,人们给梅毒起的那些名字成了一些例证,说明人们需要把那些令人恐惧的疾病当作外来的疾病。梅毒,对英国人来说,是“法国花柳病”(French pox),对巴黎人来说,是“日耳曼病”(morbus Germanicus),对佛罗伦萨人来说,是“那不勒斯病”(Naples sickness),对日本人来说,是“支那病”(Chinese disease)。
不过,这类貌似对沙文主义的不可避免性所开的玩笑却抖露出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它或许就隐藏在有关邪恶的概念中,即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non-us)、异族等同起来。污染者总是邪恶的,如玛丽·道格拉斯所言。这句话反过来说也不错:被判定为邪恶的人总是被视为或至少可能被视为污染源。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公然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
正如邻国气候中发生的剧烈变化可能波及本国一样,作为重大疾病发源地的外域,可能就是自己的邻国。疾病是一种入侵,而且的确常常是由士兵携带而来。曼佐尼这样开始他对一六三〇年瘟疫的描述(第三十一到二十七章):
卫生署官员们曾担心瘟疫会随日耳曼军队而进入米兰公国诸省,事实上,众所周知,瘟疫业已进入这些省份;同样众所周知的是,瘟疫并未止步于这些地区,而是继续前进,侵入意大利大部分国土,所到之处十室九空。
笛福对一六六五年瘟疫的记载以相似的风格开始,其中夹杂着他对瘟疫的外国来源的非常谨慎的思考:
大约是在一六六四年九月初,我和我的邻人们从别人的闲聊中听到荷兰再次发生了瘟疫;因一六六三年瘟疫就曾肆虐于该国,尤其是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两地,人们于是问,瘟疫到底来自何方呢,有些人说来自意大利,另一些人说来自黎凡特,是夹杂在货物中被土耳其船队从那儿带回到荷兰的;还有人说是来自干第亚;也有人说来自塞浦路斯。它从哪儿来并不打紧;但谁都同意说,它又回到了荷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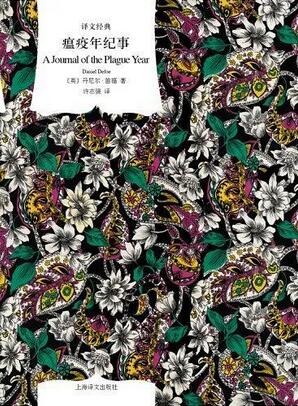
英国作家笛福所著《瘟疫年纪事》。小说描述了1665年大瘟疫袭击下的伦敦城。这本小说很可能是基于笛福的叔叔,亨利•笛福当时所留下的记录。在这本书中,笛福不厌其烦地为达到效果逼真,巨细靡遗地描述具体的社区,街道,甚至是哪几间房屋发生瘟疫。此外,它提供了伤亡数字表,并讨论各种不同记载、轶事的可信度。本书往往被跟瘟疫当代的记载相比,尤其是塞缪尔•佩皮斯的日记。笛福的记述虽然是虚构的,但比起佩皮斯的第一人称叙事,更为详细和有系统。
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再度出现在伦敦的腺鼠疫来自马赛,在十九世纪,人们总认为瘟疫是经由该城进入西欧的:由海员带来,然后由士兵和商人带到各地。到十九世纪,所谓外国来源常常带有更多的异域色彩,人们更少去具体猜想疾病传播的途径,疾病本身业已成为幽灵和象征。
在《罪与罚》结尾,拉斯柯尼科夫梦到了瘟疫:“他梦见,整个世界都遭了天谴,沦入一种从亚洲腹地而来、席卷欧洲的可怕而又奇特的新瘟疫。”在这句话的开头,使用的是“整个世界”,而到该句结尾却变成了“欧洲”,正在饱受来自亚洲的致命瘟疫之苦。
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目中的那种瘟疫无疑是霍乱,称作亚细亚霍乱,曾长期是孟加拉的地方流行病,但在十九世纪迅速成为一种世界性传染病,并且在十九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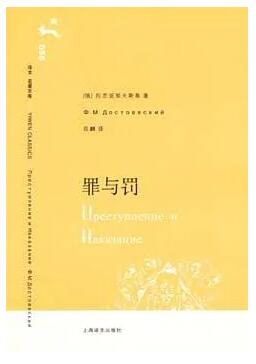
《罪与罚》系19世纪俄国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小说描写一心想成为拿破仑式的人物、认定自己是个超人的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受无政府主义思想毒害,为生活所迫,杀死放高利贷的房东老太婆和她的无辜的妹妹,制造了一起震惊全俄的凶杀案。经历了一场内心痛苦的忏悔后,他最终在基督教徒索尼雅姑娘的规劝下,投案自首,被判流放西伯利亚。作品着重表现主人公行凶后良心受到谴责,内心深感孤独、恐惧的精神状态,刻画他犯罪前后的心理变化。
几百年来流行的那种欧洲作为优越文化体的观念,包含着这么一种看法,即欧洲是一个被来自其他地区的致命疾病所殖民化的地区。欧洲自身被想当然地认为是理当免于疾病的(欧洲人对自己——以侵略者或殖民者的身份——带给异邦的、“原始的”世界的致命疾病所导致的程度大得多的毁灭,令人惊讶地不当一回事:想一想天花、流感和霍乱对美洲和澳洲原住民造成的灾难吧)。
异域来源与可怕疾病之间的顽固联系,是霍乱之所以一直比天花更令人记忆犹新的一个原因,在十九世纪,欧洲共爆发四次大霍乱,其死亡率一次比一次低,而天花灾难却随着十九世纪的推移有增无减(五十万人死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欧洲的天花流行),但天花不能被构想为一种非欧洲来源的类似瘟疫的疾病。
瘟疫不再被“带去”,如《圣经》和古希腊文献所描绘的,因为中介问题已经变得模糊了。取而代之的表述是,人们被瘟疫所“侵袭”。而且是屡遭侵袭,如笛福用来说明《大记事》系“一六六五年最后那场瘟疫袭来时伦敦所发生之事”之记事的副标题所不言而喻地显示的那样。甚至那些袭击非欧洲人的致命疾病,也可能被欧洲人称作“来袭”。但对疾病侵袭“他们”的描绘,总是不同于对疾病侵袭“我们”的描述。“我相信,半数左右的居民死于这场侵袭,”
英国旅行家亚历山大·金莱克在腺鼠疫(有时称作“东方瘟疫”)肆虐开罗之际抵达该城,写道,“然而,东方人却比欧洲人在同类的灾痛下表现出更为隐忍的态度。”金莱克这部很有影响的著作《伊欧森》(一八四四)——其富有暗示性的副标题是“东方之行带回的印记”——从这一幻象落笔,即没什么理由期盼免于灾祸的人,其感觉灾祸之能力势必萎缩,然后对众多由来已久的有关他者的那种欧洲中心主义假说进行了阐发。
A.W.金莱克(1809-1891),英国旅行作家、历史学家。他毕业于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后赴伦敦林肯律师学院学习法律。在三一学院时,他的同侪众星云集,其中包括英国桂冠诗人丁尼生。1834年,他中断学习,远赴中东,完成《日升之处》中所述的旅行。十五个月后,他回到林肯律师学院继续学业,并用七年时间完成本书。1845年,他赴北非阿尔及利亚旅行。除本书外,他还著有一部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历史著作。
于是,人们相信,亚洲人(或穷人、黑人、非洲人、穆斯林)不像欧洲人(或白人)那样感到痛苦,或那样感到悲痛。把疾病与穷人——即从社会特权阶层的角度看,社会中的异类——在想象中联系起来这一事实,也强化了疾病与外国,即与异域、通常是原始地区之间想象性的关联。
于是,为这种有关瘟疫的经典描述提供例证的艾滋病,被认为是肇始于“黑暗大陆”,然后扩散到海地,继而扩散到美国,扩散到欧洲,随后又扩散到……它被认为是一种热带病:是来自世界上大部分居民所居住的所谓第三世界的又一种侵扰,同时也是“热带的忧郁”的一场灾祸。那些从众多有关艾滋病地理起源的说法中察觉出种族主义老调的非洲人是不无道理的(同样,当他们认为那种将非洲视为艾滋病摇篮的描述势必会加深欧洲和亚洲对非洲的偏见时,他们也不无道理)。对有关原始的过去的那些观念产生的下意识联想,对疾病可能来自动物(青猴身上的病?非洲猪瘟?)传播而提出的诸多假说,都势必激活我们所熟知的那一套有关动物性、性放纵以及黑人的陈词滥调。
在艾滋病夺走成千上万生命的扎伊尔及其他中非国家,反击已经开始。那里众多的医生、学者、记者、政府官员以及其他受过教育的人相信,艾滋病病毒是从美国带到非洲来的,是细菌战的一次行动(其目标是降低非洲的人口出生率),只是该行动失控了,反过来殃及其始作俑者。对艾滋病来源的这种坚定看法,在非洲还有一个通行版本,把艾滋病病毒说成是由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军方合办的一所位于马里兰州的实验室培育出来的,然后从那儿被带到非洲,再由从非洲返回马里兰州的美国同性恋传教士带回到作为该病毒发源地的美国。

故事是以时间为脉络呈现给大家的,在阅读过程中,你将知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和获得性免疫综合征(AIDS)是如何在美国发现并扩散的,从中你将看到影响艾滋病的大量事件及各种人物,尤其是政府部门、医疗及研究机构、同性恋组织、媒体中的个体。它在以大量事实刻画人类的懦弱、绝望、自私、贪婪的同时,也以精彩的细节呈现了人类在死亡危机时的勇气、进取、无私、悲悯。
起初,人们曾设想艾滋病势必会以其在非洲出现时相同的大灾难形式广泛流行于世界其他地区,那些至今仍认为这种局面终究会发生的人援引历史上的黑死病为例。瘟疫隐喻是对流行病前景最充满悲观意味的解释的基本表达方式。从古典小说到最近的新闻报道,对瘟疫的通常描绘总提到瘟疫不可阻挡、无法避免。那些没有心理准备的人因此吓呆了,而那些留心专家们推荐的预防措施的人也同样吓坏了。
如果这种描绘出自一个全知叙事者之口,如爱伦•坡从一则有关一八三二年霍乱流行期间巴黎举办的一场舞会的报道获得灵感而创作的寓言故事《红死病的面具》(一八四二)中的情形,那所有人都将被吓垮。如果故事的叙事者是一个遭难的目击者,一个将成为屈指可数的幸存者的人,那几乎所有人也将被吓垮,如让•吉奥诺的司汤达式的小说《屋顶上的轻骑兵》(一九五一)中的情形,该小说描绘一个流亡的意大利贵族青年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穿越霍乱肆虐的法国南部地区的故事。
本文摘自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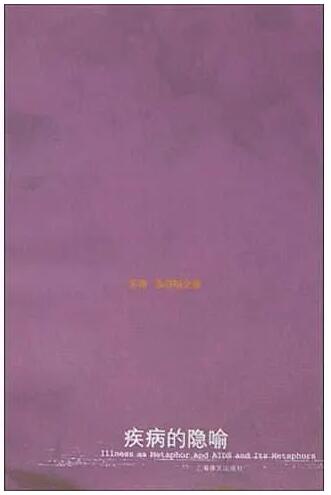
《疾病的隐喻》一书收录了桑塔格两篇重要论文“作为隐喻的疾病”及“爱滋病及其隐喻”,在文章中桑塔格反思并批判了诸如结核病、爱滋病、癌症等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文章最初连载于《纽约书评》(1978年),由于反响巨大,此后数年中两篇文章被多次集结成册出版,成为了社会批判的经典之作。
【作者介绍】

苏珊·桑塔格(英文原名:Susan Sontag,1933年1月16日—2004年12月28日),美国作家、艺术评论家。1933年生于美国纽约,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著作主要有《反对阐释》、《激进意志的风格》、《论摄影》等。
















